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经营关系研究
秦云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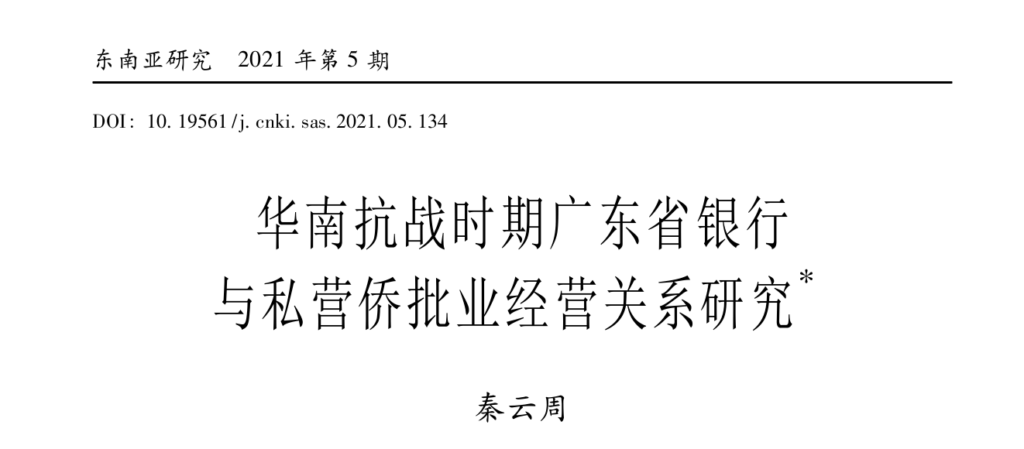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之间经营关系的研究,阐述了两者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原因、机制、成效及制约因素。研究指出,战时环境是促成广东省银行(官方金融机构)与侨批业(私营侨汇机构)合作的诱因,而互利互惠是合作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原因。合作中,广东省银行利用其官方背景和地理优势提供批路安全和资金支持,而侨批业则弥补了银行在侨汇揽收和解付环节的短板,双方的协作对充实抗战物资和赢得经济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侨批业的本质属性是逐利,且战后缺乏机制保障,双方在抗战胜利后重新走向了竞争。
论文分析了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下称“粤省行”)与私营侨批业从竞争走向合作经营的转变。研究表明,战时特殊环境是促成合作的直接诱因,而互利互惠是双方合作关系得以持续至抗战胜利的深层原因。在此合作中,粤省行利用其官方背景与地方网络优势,为侨批业提供了汇路安全保障、侨款中转及头寸接济等关键服务。相应地,侨批业弥补了粤省行在侨汇揽收与末端解付方面的短板,并为其提供了宝贵的经营管理经验。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不仅保障了数百万侨眷的生计,更为正面战场充实军备物资、赢得对日经济战乃至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牟利是侨批业的本质,与政府银行的合作限制了其利益最大化。抗战胜利后,外部威胁消失,侨批业为追求更大的汇兑利益而寻求自主经营,加之双方关系调整缺乏机制化保障,最终导致二者重回竞争与争夺的局面。
背景:战前竞争与相互利用
在华南抗战全面爆发前,广东省银行与私营侨批业在侨汇市场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与相互利用。侨批业凭借其深厚的根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而粤省行则试图利用行政力量打破这一格局。
侨批业的主导地位与对省银行的借重
私营侨批业(包括侨批局和水客)凭借其遍布海内外的经营网络和独特的经营模式,长期主导着潮汕、兴梅、海南等地的侨汇业务。作为一家新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粤省行的市场份额微不足道。
表1:1937年广东省银行与侨批业办理侨汇比较(单位:法币万元)
所在区域 | 总额 | 广东省银行 | 占比(%) | 侨批业 | 占比(%) |
潮汕、兴梅地区 | 6,200 | 194.72 | 3.1% | 5,700 | 91.9% |
海南地区 | 1,200 | 162.22 | 13.5% | 1,000 | 83.3% |
资料来源: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及广东省银行档案。 |
侨批业并未将粤省行视为严重威胁,反而利用其官方背景和金融枢纽地位,为其提供转驳侨款、接济头寸等服务。
- 寻求头寸支持:1937年抗战爆发后,潮汕、海南侨批业因缺乏法币头寸,通过同业公会及海外侨领(如李伟南)向财政部和粤省行求助。
- 利用地方优势:当日军封锁潮汕沿海,国家行局调运法币受阻时,粤省行能依托地方武装和分支网络,从陆路调运四十万法币头寸以接济侨汇。
广东省银行的限制与利用企图
作为广东省地方当局的金融执行机关,粤省行将吸收侨汇作为其核心业务,力图改变其在市场中的从属地位。由于在商业竞争中处于劣势,粤省行转而寻求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来打压侨批业。
- 核心诉求:1938年4月22日,粤省行向广东省政府呈文,指责侨批业造成国家外汇流失,并请求限制其业务:
- 结果:由于当时侨批业仍能依托其跨国网络与地方当局进行博弈,该动议最终未能实现。
核心转变:战时团结与合作
抗战局势的恶化,特别是1939年汕头的沦陷,彻底改变了粤省行与侨批业的关系,促使双方从竞争走向全面的合作经营。
合作的催化剂:战时环境与政府政策
- 中央政府政策转向:为集中全国财力抗战,国民党中央政府调整了对地方金融机构和私营侨批业的政策,从限制转向争取和团结。财政部明确指示中央、中国两行需“联络闽粤两省银行邮政汇业局及闽粤侨批业组织接受侨汇金融网”,这为粤省行与侨批业的合作提供了法理依据。
- 汕头沦陷的直接推动:1939年6月汕头沦陷,海外侨汇通过香港进入潮汕、兴梅的通道被切断,数百万侨眷生计陷入困境。私营侨批业自身无法解决汇路安全问题,而国家行局已后撤内地。在此危局下,疏通汇路的重任落在了粤省行身上。海外侨领如暹罗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明确建议:“现在救急办法,须由广东省银行迅为广设县办事处,接发侨批。”
- 日伪经济战的压力:日伪在广州、汕头等地设立机构掠夺侨汇,并威逼利诱沦陷区侨批业合作。据统计,1940年3月至1941年5月,潮汕沦陷区侨汇高达1.33多亿元法币。为对抗日伪的经济攻势,国民党中央政府愈发倚重粤省行及侨批业在国统区的联合力量。
合作的运营机制
为实现长期合作,双方在汇路安全、利益协调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建立了有效的运营机制。
- 批路安全保障:粤省行依托其官方背景和武装力量为侨批业提供安全保障。有信银庄司理芮诒壎回忆,粤省行不仅“不辞艰险,武装押运”,甚至获准让侨批局解款员工“穿着军装,荷枪实弹解款”。
- 利益协调与优惠措施:粤省行以吸收侨汇为主要目标,愿意让渡部分商业利益以换取侨批业的配合。具体措施包括:
- 减低内地汇款的运送费及手续费,合计不超过1%。
- 对批局、水客的汇款交收务求迅速,并给予优待。
- 简化批局、水客收取汇款的手续。
- 头寸供给与风险管控:粤省行遍布全省的经营网络和分区管辖制度,为其灵活调拨头寸提供了保障。同时,通过控制侨款流通的中间环节,粤省行实现了对侨批业的有效控制,确保了侨汇的最终流向。
合作领域与模式借鉴
双方的合作覆盖了侨汇的揽收、中转和解付全链条。
- 海外揽收合作:粤省行通过其在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分支机构,以及在暹罗、安南等地的通讯处,广泛联络当地侨批局和水客,吸收侨汇。
- “水客”的角色:水客成为粤省行连接偏远地区侨胞的重要助手。粤省行通过举办水客登记、简化取款手续、提供妥善招待等方式,充分发挥了水客“无论任何山僻小地,均必亲自前往”的优势。
表2:1941年梅县出洋水客分布区域与人数
所在地区 | 人数 (人) | 占比 (%) | 所在地区 | 人数 (人) | 占比 (%) |
荷属爪哇 | 242 | 50.6% | 马来亚 (新加坡各埠) | 125 | 26.2% |
荷属坤甸 | 18 | 3.8% | 荷属坤甸 | 35 | 7.3% |
加里吉打 | 10 | 2.1% | 荷属苏门答腊 (日里) | 10 | 2.1% |
帝汶历唎 | 12 | 2.5% | 文岛 | 9 | 1.9% |
毛里西亚 | 8 | 1.7% | 勿里洞 | 4 | 0.8% |
安南 | 4 | 0.8% | 布旺 | 1 | 0.2% |
资料来源:谢复生编《梅县要览》。 |
- 学习借鉴侨批业模式:粤省行积极学习侨批业“信款合一”、服务至上的经营模式。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明确要求省行“效法批局、水客,极力便利侨汇”。具体做法包括:
- 简化流程:仿照批局办法,举办水客登记,简化取款手续。
- 提升服务:推出特约汇款、侨汇贷款、侨胞家属登记等服务,切实降低汇费。
- 送款下乡:尝试仿效民信局,将款项送至乡间。
合作典范:东兴汇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兴汇路的开辟与维持,成为广东省银行与侨批业合作的典范,体现了公私机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高效协作。
太平洋战争前的探索
- 网络预置:粤省行早在1939年10月就在毗邻越南的东兴设立办事处,为后续侨汇流通打下基础。
- 建立关键伙伴关系:粤省行与潮汕侨批业翘楚“魏启峰批局”建立了紧密的协作关系。魏启峰批局以大量存款支持粤省行揭阳办事处(揭处)业务,并代为交付偏远地区侨批;揭处则为其提供转汇、头寸接济及武装护送等服务。1941年,双方正式签署交兑汇款合约。
太平洋战争后的有效运转
- 成为生命线: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海上侨路中断。东兴汇路成为暹罗、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侨汇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
- 分工协作:
- 侨批业负责海外段:侨批业利用其灵活隐蔽的网络,在暹罗及印支联邦收集侨款,集中至越南海防或河内,再秘密运至东兴。
- 粤省行负责国内段:侨款到达东兴后,通过粤省行东兴办事处及其国内经营网络,转驳至粤东、闽南地区。粤省行为合作的批局提供汇路安全保障和关键的头寸接济。
- 魏启峰批局的核心作用:凭借与粤省行的良好合作及自身的海外网络,魏启峰批局成为东兴汇路的主力。据估计,“1942年春以后,由魏启峰批局接转的批款,几乎占东兴汇路汇入揭阳批款总额的70%”。
- 汇路中断:1944年11月,因日军入侵,东兴危急,粤省行办事处及侨批业撤退,东兴汇路陷入低潮,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复业。
合作的成效与制约因素
广东省银行与侨批业的战时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受到来自国家政策和自身属性的内在制约。
显著成效
- 经济贡献巨大:从1939年到1945年,粤省行办理的侨汇总额高达24亿多法币,约合9651万美元,约为同期中国银行办理总额的35%。作为一个地方性银行,能取得如此成就是非常不易的。
表3:1939—1945年广东省银行与中国银行办理侨汇数额比较
年度 | 广东省银行 (法币元) | 广东省银行 (万美元) | 中国银行 (法币元) | 中国银行 (万美元) |
1939 | 30,522,778 | 908 | 173,570,000 | 5,163 |
1940 | 83,223,551 | 2,476 | 222,300,000 | 6,614 |
1941 | 78,710,563 | 418 | 112,130,000 | 639 |
1942 | 141,542,247 | 732 | 431,040,000 | 2,229 |
1943 | 408,575,087 | 2,057 | 1,206,790,000 | 6,075 |
1944 | 683,901,240 | 1,710 | 741,280,000 | 3,740 |
1945 | 1,000,134,027 | 1,350 | 682,070,000 | 3,424 |
合计 | 2,464,333,600 | 9,651 | 3,569,180,000 | 27,884 |
- 战略意义深远:
- 支持抗战:为国民政府充实了外汇储备,为购置军事装备、稳定法币币值提供了保障。
- 赢得经济战:有效对抗了日伪在华南掠夺侨汇的图谋。日方资料显示,由于“重庆政府彻底地实行了引诱吸纳华侨资金的工作”,其在1941年7月后经汕头吸收的侨汇“几近绝迹”。
- 稳定社会:维持了数百万侨眷的生计,维护了战时广东的社会稳定。著名学者饶宗颐对此高度评价:“抗战期间能保持侨汇之流通者与有功焉。”
内在制约
- 中央政府的限制: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核心目标是维护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国家行局的主导地位。因此,在利用粤省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限制和防范。
- 限制海外扩张:财政部严格限制地方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导致粤省行“原拟在美洲南洋各地普遍推设行处”的计划未能实现,极大地限制了其海外揽收能力。
- 业务干预:粤省行新加坡分行仿照民信局开办的“汇款带信”业务,因影响到中国银行的利益和邮政部门的邮资收入而被迫取缔。
- 公营机构的局限性:
- 经营模式差异:粤省行作为现代金融机构,其经营基于“对物的信任”,无法完全复制侨批业基于“对人的信任”的灵活模式。其简化的手续仍需殷实铺保,反而可能增加侨眷负担。
- 效果有限:由于侨眷对公办行局的防范心理,粤省行推出的侨胞家属登记、借款等服务收效甚微。例如,松口地区有四万侨胞,但截至1941年3月,家属登记仅45户。
结论:战时共生与战后分离
华南抗战时期广东省银行与侨批业的合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互利共生关系。战时环境的威胁和共同的利益需求是双方合作的基石。侨批业通过与粤省行合作,利用其政府背景和网络优势,有效规避了经营风险,维护了商业利益。粤省行则借助侨批业的网络和经验,突破了自身在侨汇业务上的瓶颈,为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然而,这种合作本质上是临时的、策略性的。侨批业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与政府银行的合作必然以牺牲部分商业利益为代价。抗战胜利后,外部威胁解除,侨批业寻求自主经营以获取更大利益的动力增强。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机制来调整双方的战后关系,二者不可避免地重新走向了竞争和争夺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