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佬的来信及其他随笔》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严元章藏书0156
《一个中国佬的来信及其他随笔》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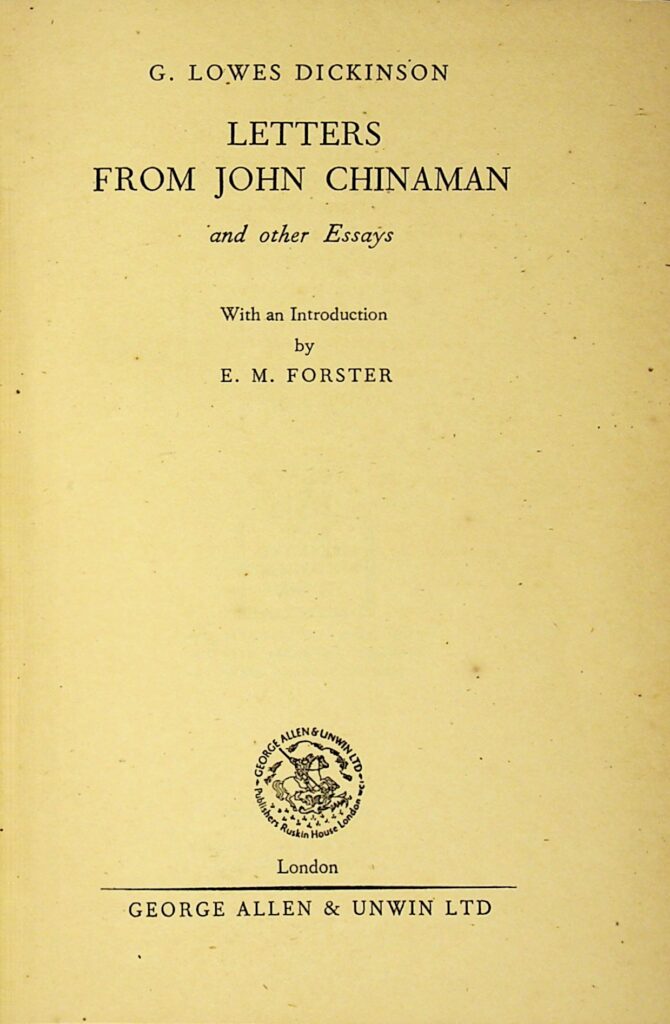
《一个中国佬的来信及其他随笔》包含 《中国佬的来信》 和 《论印度、中国和日本文明》 两部著作,以及一篇关于 古希腊对现代生活贡献 的演讲。 《中国佬的来信》 从一位中国观察者的角度,对西方文明的 道德、经济和政治方面 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解释了中国文化及其排除西方影响的原因,强调了中国社会对 家庭、道德和精神价值 的重视。 《论印度、中国和日本文明》 则是一篇比较文明的随笔,重点探讨了 印度和中国文明 的根本差异,指出印度以 宗教 为主导,而中国以 人本主义和世俗精神 为特征,并分析了它们各自对 现代西方影响 的反应。最后,关于 古希腊的贡献 的文章赞扬了希腊文学的 永恒性 和希腊思想的 启发性,尤其关注其对西方世界 科学与伦理 发展的作用,并探讨了 宗教、信仰和不朽 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本书是G. Lowes Dickinson(1862-1932)的著作选集,于1946年首次以现有形式出版,并收录了E. M. Forster所作的引言。Dickinson本人是一位剑桥大学的院士、学者、哲学家,甚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一生关注公共事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感到震惊,并积极推动国际联盟的建立,被认为是其发起人之一。Forster指出,本书很好地体现了Dickinson对东方、宗教和古希腊文明的浓厚兴趣。他信奉理性、正直、宽容、同情、爱和艺术。
一、《一个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这篇写于1901年的作品是Dickinson较短作品中最著名的一篇,创作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和欧洲远征镇压时期。他对中国展现出的深刻同情和洞察力,为他在中国赢得了持久的声誉。
在书信开篇,作者便指出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最稳定的文明,其本质体现了道德秩序(儒家思想),而西方文明则体现了经济混乱。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强调伦理关系和稳定,人们尊重过去,懂得欣赏自然之美。相比之下,西方社会以个体为单位,追求进步、财富和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现金关系”,导致社会动荡不安。Dickinson批评西方人民被隔绝于自然之外,缺乏艺术,徒有知识却未经教育,道德和宗教流于形式,只关注物质目标,最终沦为社会机器的工具。
他阐述了中国抵制西方的原因: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均自给自足,不寻求对外传教或贸易。而西方则因其宗教优越感和对海外市场的经济需求(生存问题)驱动而进行侵略。作者认为,西方经济体系的本质混乱且充满“不负责任”(irresponsibility),并预言商业竞争将最终导致欧洲国家间的战争,他们“必须吞噬或被吞噬”。他赞扬了中国社会中的受教育阶层致力于精神追求,他们珍视艺术、文学以及对简朴生活的欣赏。
在治理理念上,虽然中国官员存在腐败问题,但Dickinson认为其危害小于西方,因为中国社会主要依靠家庭和习俗维持,中央政府的影响力较小,法律是民族生命的“公式”。他批评西方的代议制政府依赖武断的规则,社会被瓦解,选举代表的是利益集团,而非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行治理。
关于宗教,儒家思想是中国的社会基础,本质上是伦理道德系统,强调家庭与国家的统一以及“劳动理想”。他认为基督教的理想是“沉思”而非劳动,强调“圣徒的交通”,与西方社会结构本质上的世俗性不相容。他指出西方国家以基督之名对中国采取的暴力行为,恰恰证明了其信仰与其公共政策的脱节。他引用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证言,称赞中国人“崇尚理性,相信公理,以至于不屑于认为公理需要武力支持或强制执行”。
信的结尾,作者解释了中国的暴力行为源于西方强烈的挑衅和侵略,例如鸦片贸易、不平等条约和传教士干预。他呼吁西方将中国视为文明大国,尊重其习俗和法律,否则不会有和平。
二、《论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An Essay on the Civilisations of India, China, and Japan)
这篇随笔是Dickinson作为阿尔伯特·卡恩旅行基金研究员(1912年至1913年)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东方”并非统一体,印度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一道深刻的鸿沟。他总结了三大文明的基调:印度是宗教;中国是人道;日本是骑士精神(武士道)。
第一部分:印度
印度文明的主导特质是宗教,其核心在于相信真生活是精神生活,而物质世界是“虚幻”。这种宗教是“不人道的”(inhuman),与西方的关注点不同,它更关注普遍的心灵和精神。印度艺术表达的是“自然的不屈不挠和非理性”。印度是悲观主义的,寻求从世间的活动中解脱,其社会结构由种姓制度主导。
Dickinson观察到,英国人是所有西方民族中最不善于欣赏印度文明特质的。英国统治维持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几乎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英国在印度的教育,虽然传授了民主自治的政治理念,却与英国在印度的专制统治相矛盾。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中,民族自我意识在增长,开始反对西方理念。西方的工业主义和铁路正在逐渐瓦解种姓制度,同时改变了印度妇女的地位。印度艺术和手工艺品的衰落不仅是因为西方商品的竞争,也是因为本地精英缺乏品味,转而青睐劣质的西方艺术。他总结认为,印度从西方接触中可获得更多,可损失更少。
第二部分:中国
与印度截然不同,中国是人道的、开朗、富有活力,其文明本质上是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注重行为规范。中国的艺术是“人类的”,反映了对人道生活和自然美的敏感欣赏。中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调平等机会的民主国家,不存在种姓制度。
Dickinson认为中国与现代西方有着根本上的相似性:世俗、务实、讲求实际。西方化所需的只是新的技术。西方影响起初集中在通商口岸,但正在迅速渗透。新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领袖(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接受教育的)极力推动革命,渴望彻底改变旧中国,但他们普遍缺乏经验、品格和强大的民族政治意识。然而,教育进程已经开始,他认为,无论政治形式如何,旧中国都已成为历史,西方的思想渗透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部分:日本
日本在气质上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健康优美,艺术精致普遍,但缺乏希腊的理性能力(哲学和科学)。革命前的日本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翻版,主导基调是骑士精神(武士道),以对天皇及其祖先的忠诚(神道教)为核心。日本通过自我西方化避免了被西方征服。这种转变导致了审美趣味的毁灭,一切变得丑陋和俗气。西方工业系统的引入带来了贫困、失业和工厂剥削等欧洲式的社会弊病。日本政府采用德国模式,是专制且官僚化的,压制结社和言论自由。Dickinson认为这种将工业文明、新闻自由与专制统治相结合的体系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结论
Dickinson总结,东方发展出了一种西方现代世界已丧失的生活类型(例如以土地为基础的生活和沉思文化)。西方擅长“生活的机械”(应用科学),提高了物质舒适度,但牺牲了生活的美感和沉思能力。他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东方难以只选择西方的技术而不承受其社会混乱和丑陋。他预测,西方将在内部寻求平衡,而东方在恢复真正精神生活之前,将不得不经历西方所经历的所有物质主义的过度阶段。
三、《古希腊对现代生活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Ancient Greece to Modern Life)
这是Dickinson于1932年在剑桥暑期学校发表的讲座。他将古希腊的贡献分为文学(永久的财富)和思想(反复的刺激)。
在文学方面,希腊文学具有永恒的新鲜感,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做出这些成就的文明。他通过阿里斯托芬的《蛙》等作品,对比了埃斯库罗斯(英雄主义)和欧里庇得斯(现代民主主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风格。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被赞扬兼具诗意和欢笑。希腊也是散文的大师,如希罗多德(历史学家)和修昔底德(对战争的社会和心理影响的分析在现代仍具现实意义)。柏拉图是伟大的作家和对话体的发明者,他试图捕捉苏格拉底的谈话精神。
在思想方面,希腊人是伟大的创始者,早期的思想家是非专业的,集政治家、军人、发明家、哲学家于一身。亚里士多德奠定了逻辑学和生物学等基础;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古希腊科学面临着科学与宗教的冲突:苏格拉底/柏拉图反对自然科学,转而关注价值。由于缺乏实用性,古希腊科学最终衰落和消亡。Dickinson总结,现代文明正面临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相似的困境:科学与伦理的冲突,解决之道在于将伦理应用于科学,将科学应用于伦理,调和对立面。
四、《宗教:批判与预测》(Religion: A Criticism and a Forecast)
该系列随笔主要探讨宗教与知识的关系。
第一章 论教会主义: Dickinson认为知识的唯一方法是经验和合理的推论。他将教会主义定义为宗教声称拥有人类理性无法获得的真理,并通过诉诸情感、偏见和习俗来传播教义的组织。教会主义试图故意固化思想和品格,使人对理性免疫,虽然它能维护社会稳定,但其代价是扼杀理性、阻碍增长。他指出,如耶稣会士的训练所示,教会主义的目的是“事先麻痹可能干扰(既有氛围)的机构”,使人将理性和才能服从于信仰,从而遏制增长。真正的教育目标,应是如柏拉图所言,在培养健康本能的同时,自由地发展理解力,让理解力成为最终的评判者。
第二章 论启示: Dickinson质疑“启示”作为一种独立于理性的权威性的来源。他认为历史事实的真伪必须由历史批判来确定,不能通过“启示”来获取。瞬间的直觉或“皈依”经验,由于可能只是情感反映或与疾病产生的幻觉无异,不能作为真理的证明,其有效性必须通过批判性测试来验证。他总结,宗教的职能不应是宣告关于宇宙结构的真理;那是科学的责任。
第三章 论宗教: 宗教被重新定义为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形势的一种想象力与情感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以我们的理想为视角的。真理属于科学,而宗教属于想象和情感。如果世界被视为冷漠或恶劣,宗教可能表现为挑战或弃绝;如果世界朝向良善,宗教则表现为乐观;如果知识停留在不可知论,宗教则表现为一种“星光黄昏”般的冒险精神。他强调,道德改革起源于宗教洞察力,宗教是道德的“精神和生命”。艺术与宗教结合,可以达到最高的意义,如希腊和意大利艺术史中所体现,宗教通过建筑和仪式获得表达。
第四章 论信仰: Dickinson认为,神学真理若可求,也是科学或哲学的真理。他将信仰(Faith)定义为一种情感和意志上的假设,它在知识的匮乏中运作,与不可知论兼容。信仰的本质是假设事物“值得付出”(worth-whileness),并以此为中心指导情感和行为。信仰必须在未被知识征服的领域内运作,并随时准备为知识让位,否则便是最灾难性的不道德行为。信仰是想象和意志的产物,是探索者心中的梦想和希望,是“开放地平线的感知与召唤”。
五、《宗教与不朽》(Religion and Immortality)
第一节 信仰与知识: 他认为,现代自由思想家正在信仰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神话。他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是不够的,因为它被教义固化,且其宇宙观(如创世论)和伦理观(如原罪)对现代人来说已不再可信或不适用。新的信仰必须将人类的生命和理想与宇宙相协调,应当强调力量和自我尊重。
第二节 乐观主义与不朽: 乐观主义是一种本能的信念,认为生活是“值得付出的”。理性上支持乐观主义,要求相信世界是一个朝向良好目的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永恒完美的。他指出,种族进步的理论是不足以支撑乐观主义的,因为它将个体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他坚信,西方乐观主义要持续,必须假设个体生命具有超越现世的意义,即不朽。
第三节 不朽是否值得期望? (1909年哈佛大学英格索尔讲座)。Dickinson将不朽视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科学否定不朽是基于心智与大脑的联系,但这并非逻辑上的必然结论;肉体可能是灵魂的居所。他排除了大多数人的冷漠态度,也排除了尼采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因为后者只有对于“有价值的生命”才是可取的。传统的基督教不朽观**(包含地狱和永恒惩罚)因不符合现代人道主义和对乐观主义的诉求而被拒绝。他认为不朽是值得期望的,因为人类的“灵魂”总是在寻求**“更多、更好的生命”,寻求实现现世中未曾实现的潜能和理想。他总结,这种值得期望的不朽是一种有意识的持续存在**,是持续展开良善潜能的不朽。
第四节 安乐死(笔记): 本节体现了作者的神秘主义倾向。作者描述了一种知觉与想象界限模糊的体验,他体认到万物皆有生命,生命是被追求良善的力量所驱动,从不和谐走向和谐。人被囚禁于肉体(“一个壳”),只有死亡才能打破牢笼,使灵魂实现其潜能。他通过回顾前世经历和感受日出,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并感受到灵魂挣脱肉体,走向新的不朽。


